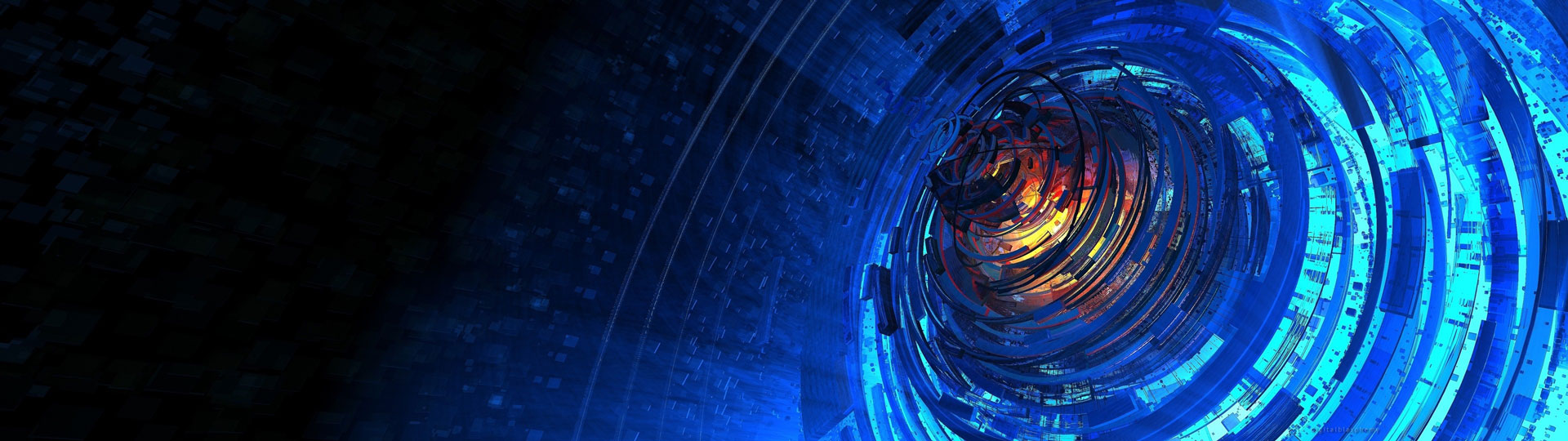
中唐以前,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主要依靠血缘关系维持,门阀士族把持着社会的上升通道,一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家族。中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宋代,随着科举的兴起和发达,寒门士子,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可随着科举考试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考中的几率必然越来越小。而且即便考上了进士,进了官场,因为进士的数量越积越多,普通士人想要在仕途上出人头地,也是越来越难如登天。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压力之大,远超汉唐的读书人。因为汉唐讲阀阅,身份决定命运,个人很难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大家只能认命。而宋代的科举社会,给了普通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大家有资格不甘心了,可这个机会又越来越小,让大家又都卷得厉害。宋代读书应举的人之多,以至于哪怕是在乡野荒州,也有许多人做着鲤鱼跳龙门的美梦。如何让士人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算命术对他们而言,就是最有效的心灵安慰。
为了缓解对前途的担忧以及内心的紧张感,士子们在考试前都会去请术士给自己算一下命,很多术士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商机。据说宋代开封城中的“卖卜者”,最赚钱的地方就是“举场”。举子每逢大考,都要跑去算下命,算命先生们则是采取专挑好话说的策略赢得士子们的青睐——“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就是只要问这场科举中还是不中,得到的回答都是必中。这样“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于是生意爆棚。当然,这种投其所好的“骗术”比较低级,也就是给士子们一个心理安慰,算命先生表面上收的是算命钱,实际上收的是“心理咨询费”。
更高明的术士,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参加考试的人多,录取率很小,如果见人都说必中,那么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毕竟考完之后,还是落第者居多嘛。事后觉得他算得不准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其口碑自然会越来越差,这钱就不好挣了。
后来有位术士发现,与其讨好士子们,降低自己预言的命中率,还不如“凡有人问,悉曰不得”。这真是天才的办法,考完之后,考不中的占绝大多数,事后大家一想,觉得这个算命先生算得就是准,算命技术就是好,而且为人还耿直,敢于说真话。于是,他的人设一下子就立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为著名的卜者,并靠这个赚得盆满钵满,“终身飨利”。被誉为现代最早发现“石油”的人沈括,后来也发现了这个秘密,并把这个事情写到了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里。
其实对于大多数考不上科举的士人,相信命运的安排,也是一个不错的心理安慰法。宋人陆九韶曾说:“世之教子,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
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有的人就可以及时从科举中抽身,不致把一辈子的幸福都耗在科举之上,失去人生之乐趣。如南宋时出身明州大族的周伯范,他经过一次科举失败后,就认定自己没有中举的命,于是决定放弃科举——“一举不遂,即弃举子业,一意世学,翻经阅史,几不释卷。以为名第有命,不可强求,不坠家声足矣。”此后他“经理家务,井井有条”,日子过得也红红火火,还有余力出资救助穷苦,修桥铺路,成为远近之间受人爱戴的乡贤。([宋]楼钥:《攻媿集》卷一百九《周伯范墓志铭》)
士人们需要从算命中获得精神支持,而宋代以算命为业的人又很多,恰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王安石说,当时以算命为生的人,全天下恐怕数万人不止,这还不包括京城开封的人数。这一行在开封的从业者数量巨大,光开封一地,就“盖以万计”。王安石发现他们中,有“挟奇术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知名的算命先生,住豪宅、穿华服,吃香喝辣,不亦乐乎!
他分析说,京城中之所以算命生意这么火爆,是因为有些人缺什么就想什么,常言道,“渴者期于浆,疾者期于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文人士大夫读书应举,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还想当大官;当了大官的,又怕当不长。这些人怕这怕那,想不明白就会担惊受怕,遇事就会拿不定主意,这时就巴不得有人来帮忙做决定,正所谓“势不盈,位不充,则热中,热中则惑。势盈位充矣,则病失之,病失之则忧。惑且忧,则思决。”文人士大夫热衷于算命,是因为“以彼为能决”,当他们没法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做决定,就只能求神问卜了。([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汴说》)
宋人有“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的说法([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科举时代带给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困境,还不止科举考试本身的问题。即便他们考上了进士,做了官,官场的风波,也是他们难以预料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给予文人士大夫最大的福利,可是当官也不一定能够富贵荣华一生。今夜高朋满座,明朝妻离子散,也是宋代许多达官贵人的常态。
邵伯温与长安术士张衍有些交情,为人忠信、识道理,算命之准,令人拍案称奇。据说在章惇、蔡确还在当县官的时候,张衍就给他们批命说二人必能当上宰相。作为术士,张衍最厉害的还不是算得准,而是意识到身处新时代的士大夫命运无常,有些人即便是有大富大贵之命,也难以善终。他说:“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简单地说,就是贵人有大富大贵的命,但所得的富贵能享受多久,并没有保障,对他们而言,难的是善始善终。
为什么呢?他告诉邵伯温:“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六)这是他在官场多年观察下来的经验之谈。
如何理解张衍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以前的士大夫,好的命格是层次分明的:命最好的,当宰相,位高权重;稍次一点的,可以当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再次一点,就只能当九寺三监的长官;最次的一等,也可以当路级和州级的地方官。这是因为以前人当官是循序渐进的,整个官僚队伍里面,最后能混到金字塔顶端当上大官的人不多。这就是贵人少的原因。大家即便按部就班地当官,也能各自混到一定的级别,吃喝不愁、安享晚年,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现在的士大夫所在的官场,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现在当大官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升官也比以前快了,甚至得到破格提拔的机会也多了。昨天还是小官,今天便当大官,但是没过几天,又被弹劾罢官,当官纯属是过过干瘾,对自己和家族都没什么好处。因为当大官这种大富大贵的命,都是暂时的,自己的富贵难保长久,子孙的福禄也没有保障。大起大落的富贵命,到最后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张衍从八字命理之说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的贵命,多是靠着“刑杀”才得的富贵,所以难以持久,过不了多久就会招来灾祸。八字命理中所谓的“刑”,指的是八字中地支之间出现互相伤害的情况,如寅刑巳,巳刑申,刑害又有无恩、无礼之分,如寅刑巳,巳刑申是为无恩。《三命通会》的解释是:“盖寅中有甲木刑巳中戊土,戊以癸水相合为要,则癸水者,甲木之母也,戊土既为癸水之夫,乃甲之父也,彼父而我刑之,恩斯忘矣”。
八字中有刑害,对命格必有损伤,本不是好事。但在某些情况下又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即“相刑遇贵”,如“寅刑巳,巳刑申,庚辛逢寅是贵人”。有的时候,刑带三奇、贵人、天德,则贵不可言,正所谓“三刑之位带三奇,天乙兼得在日时,刑若等分干遇德,官居极品定无亏”。
所谓的“杀”,指的是“七杀”,又名“偏官”,是八字中的天干出现阴阳不相配的情况,本为凶命之格。宋代徐子平所著的八字命理著作《渊海子平》中说:“夫偏官者,甲木见庚金之类。阳见阳,阴见阴,乃谓之偏官,不成配偶。”命中带七杀,易招横祸。但如“制伏得位,运复经行制伏之乡,此大贵之命也”。总的来说,以刑杀得来的富贵,是有些凶险的,来得快,也去得快。也就是张衍所说的“贵人多,福人少”。
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人不同,命也不同。这个故事里,隐隐约约体现出算命术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觉悟。张衍的观察并非特例,很多算命先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南宋初年的张端义说,近年来,临安的老年术士以前因为算命算得好,赚了不少钱,现在生意都不行了,因为老了之后,他们就算不准了。但年轻一辈的术士,算命又都算得准,他们生意好得很。有一次有个老年术士问年轻术士,说:“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大家都是用的同样的方法算命,为什么之前灵,现在就不灵了呢?
年轻的术士回答说,那是因为:“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守帅阃者,日以杀人为事,汝之术所以不验也。”([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八字算命,以生辰干支的五行生克构造所谓的吉凶祸福,所谓禄、贵、生、旺,即是五行配合得宜的。如“禄,爵禄也,当得势而享,乃谓之禄”。具体的看法是,“十干就支神为禄,谓禄随旺行,所以甲禄寅、乙禄卯”之类,以“甲禄寅”为例,“甲见丙寅,甲土克丙水财,为福星禄;戊寅火土相生,为伏马禄,俱吉。”([明]万民英:《三命通会》卷三)
禄、贵、生、旺的看命法,是正常的贵命看法,以前的算命先生看命,就先看一个人的八字中有没有禄、贵、生、旺的格局。但年轻的术士却认为,老年术士算命的方法,用的是面对正常世道、正常人情况时的算法,可现在世道不古,人也不正常,所以之前那套算法就不管用了。
八字命理学中,刑杀冲击本来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正如前面那个故事里所讲那样,理论上“刑杀”也可以构成贵命之格。前文已解释过,所谓刑杀乃是八字理论中的地支相刑和天干相杀,而非这个年轻术士所说当官的一天就是抓人杀人,以此搏富贵。当今士大夫,要多带刑杀冲击,才能成贵人之命的说法,显然是借题发挥。他这么说,是在讽刺当今的士大夫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升官发财。
文人士大夫从小读圣贤之书,儒家本来的道理,是“用舍无预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士大夫面临选择困难的时候,应该以义理为准绳,用算命的方法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方向性的错误,是“贪冒无耻者”用来自欺欺人的托词罢了。朱熹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盖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了。虽使前面做得去,若义去不得,也只不做”。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而是要以“义”为先,“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
朱熹举了孔子著名的弟子颜回的例子,他说:“如颜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计较命如何?”颜回就不会去算命,因为他只做义理上该做的事,至于个人的功名富贵,从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能做到“安于陋巷”。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一心追求升官发财,把圣贤理想都忘得一干二净的士大夫,才是最迷恋算命的群体。
作者:黄博
来源:《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时间:2023年07月
出版方: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