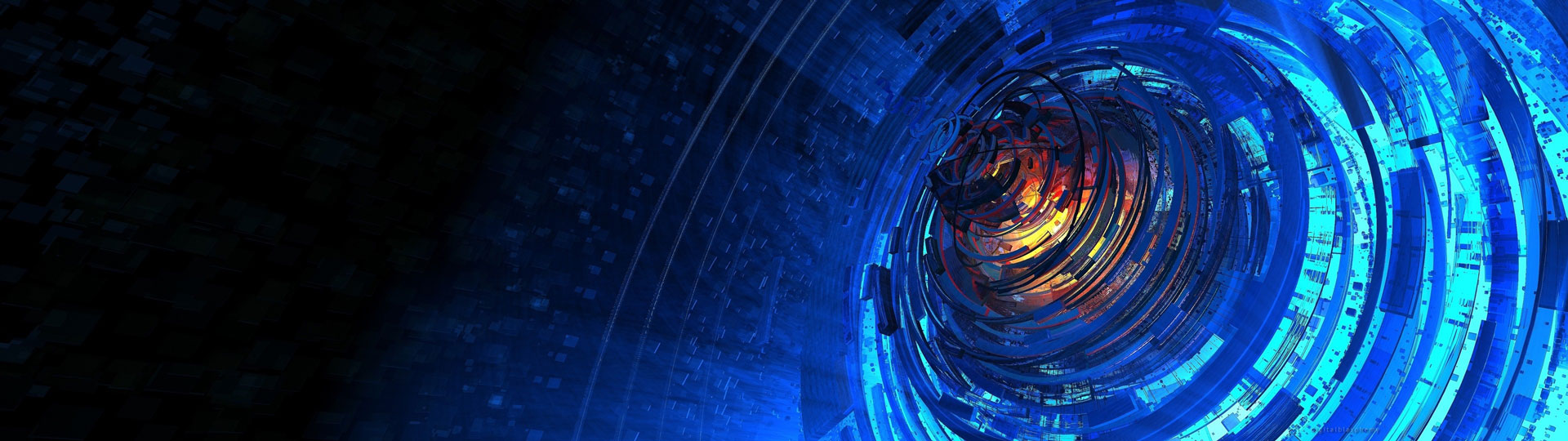
软肋证据”是指以被告人子女的合法权益相威胁取得的供述。以被告人的子女相威胁,在威胁程度和烈度较低的情况下,就足以使被告人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违背意愿作出供述。该论断的依据是:在我国传统上,子女比其他近亲属有更加特殊的伦理和法律地位;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观当中,子女承载了父母最为深厚的情感寄托。“软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公共性,法律应该成为“软肋”们最坚强的后盾,而不是容忍其成为审讯策略的一部分。“软肋证据”不必评估威胁程度,只要触及就应当一概排除。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题记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严格排非规定》)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的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被告人供述的排非范围。因为在此之前,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只有基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才能排除,威胁被告人则是一种法律容忍的审讯策略。
但是,对于何为“难以忍受的痛苦”,法律并无明确标准。因此,《严格排非规定》实施至今,公开的裁判文书尚无据此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实际上,正如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认定一样,很难形成统一的裁量标准,本文无意给出可靠的方案,而是旨在提出,有一些威胁手段,由于精准击中被告人的软肋或者弱点,即使威胁的程度和烈度较低,也足以对其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违背意愿做出供述,损害口供的真实性。
诚然,每个人的软肋是不一样的,但基于现有案例、文化传统以及公共政策,我们发现,子女几乎是所有国人的软肋,对于以此威胁被告人取得的供述,可称之为“软肋证据”,对于“软肋证据”,应当不评估威胁权益的严重程度而直接排除。
试举以下三个案例分析说明:
案例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候选人金成俊受贿、滥用职权案。金成俊在陈述其遭受的非法取证时,称办案人员威胁“抓其儿子作为共犯,让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的威胁所带来的痛苦不亚于刑讯逼供的痛苦,遂做出虚假供认。【(2022)皖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案件已审结】。
案例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原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新添寨派出所代理所长刘玉冰贪污、滥用职权案。其中关键证人系该派出所的会计周某飞,其接受讯问时正在怀孕,被办案人员以搞掉腹中胎儿相威胁,其遂做出供述,即使历经一审、二审也未能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2021)黔01刑终429号刑事裁定书,案件已审结】。
案例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郑祖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被告人郑祖文在“不认则抓人(女儿女婿),认了就放人”的强烈心理恐惧下,做出虚假供认。据此,相关供述经一审法院排除,后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威胁行为是侦查策略。最终该抗诉意见没有获得二审法院支持,原因是“郑祖文被讯问时已退休近10年、年近70岁,因个人的原因导致女儿、女婿(公职人员)被检察机关“抓起来”,这对其心理必然起到强烈的胁迫作用,迫使他为保住一家老小的平安,选择做出牺牲,违背意愿作出有罪供述。这种以针对被告人本人及其亲属的重大不利相威胁,产生的精神强制效力达到了严重程度,极大可能导致被告人精神痛苦并违背意志进行供述。”【《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140号]】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以损害被告人子女的合法权益相威胁取得被告人的供述,但每个案例都独具特点。
第一个案例中,金成俊遭受了刑讯逼供、其本人的合法权益遭到威胁、其被以严重损害妻儿的合法权益相威胁。换句话说,法律规定的非法取证类型他都承受过,哪种手段带来的身体或精神痛苦更强烈,他最有发言权。
第二个案例中,周某飞被以腹中胎儿相威胁,相当于本人和未出世的子女一并被威胁,对于未出世的子女来说,属于以生命相威胁,威胁程度不可谓不严重,对任何常人来说不可谓不痛苦,但这是2021年审理的案件,竟未启动排非程序。
第三个案例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该案2012年审理,彼时的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尚无威胁近亲属供述排除的规定(这也是一审检察机关主张不排非的理由),但广州中院和广东高院就极具前瞻性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通过解释法律排除了相关证据。
综合三个案例来看,司法机关对于何为“难以忍受的痛苦”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在常人看来已经很痛苦的威胁却不被认定为痛苦(当然从逻辑上看可能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前述,本文无意于划定标准,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所要主张的命题是:“软肋证据”无须标准——以被告人的子女相威胁,不需要前置判断威胁的严重程度和被告人的痛苦程度,就应当直接做出排非决定,以杜绝这种有违伦常道义的做法,同时也能避免法官利用判断痛苦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把常人都觉得很痛苦的威胁认定为不痛苦。
二、从我国传统上看,子女比其他近亲属有更加特殊的伦理和法律地位
从文化习惯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与欧美不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人际关系存在“差序格局”的特点,该观点目前已被广泛接受。这说明,中国人的意识里不同序位的人有重要性差别。而“差序格局”所描述的圈层制,显然与古代长期采用的“五服”亲等存在交叉。但不论是“服制”还是“差序格局”特点,实际上都是以“己身”为中心,对普遍的亲疏关系所做的制度化和规律化总结,背后本质上还是“人心”,于是同样的威胁加之于不同的亲属,当然会产生不同效果,可以说,越亲近“威胁效果”越好。
值得注意的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在亲属关系中地位特殊。《汉书宣帝纪》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此外,《刑案汇览》记载了清道光二年的一个案例,父亲为儿子报仇,擅自将行凶者杀害,司法官员认为“何重布系为伊子复仇所致, 较其余亲属更为激切”,在量刑时作为考量。可以看出,传统中所谓“虽有祸患,仍愿舍身相救”“为子复仇,更为激切”,这种情感又何须论证,正如郑祖文案中法官所论述的,“因个人的原因导致女儿、女婿(公职人员)被检察机关“抓起来”,这对其心理必然起到强烈的胁迫作用,迫使被告人为保住一家老小的平安,选择做出牺牲”,如此威胁之下,何患无辞。
而“独子”则有着更特殊的法律地位。古代“存留养亲”制度为人所熟知,即徒流罪犯家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疾病而无其他男丁侍养者,得停止或免除刑罚的执行,返家侍养其亲。这是儒家哲学思想的伦理观念深嵌于司法实践的突出表现。但该制度有个例外,如果行为人因杀害他人独子而获刑,则不被允许适用。根据《大清律例》存留养亲制度的规定,犯人符合留养条件后,要查明被害者是否为家里的独子,若是家中独子,则不准犯人留养;若受害者虽为家中独子,但是平日游荡在外未尽孝道不赡养家中亲人,则准许犯人留养。可见,独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地位更为特殊和重要,伤人独子将在礼法上遭到更严厉的谴责(当代社会,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情感纽带以及法律地位相同,本文是基于当代视角回溯传统礼法,不再赘述儿子和女儿在法律地位上的古今差异)。
三、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观当中,子女承载了父母最为深厚的情感寄托
从当代家庭结构来看,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家庭人口老龄化及相应的居住模式变化、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是我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主要趋势。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以及同胞兄弟姊妹,但家庭规模小型化意味着核心家庭组成成员一般限于父母与子女,这与长期执行的一孩政策以及目前少子化趋势存在一定的关联,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与关注随着一段时期内“少生优生”和“优生优育”的理念明显加重。因此,应当注意到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子女之于父母,在整个近亲属范围里,是更为特殊的存在,他们几乎承载着父母全部关爱和精神寄托,尤其在独生子女家庭这种情感更甚至。
显然,对于该群体,不用施加过度威胁就足以对被告人造成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从而违背意愿和事实做出供述,损害供述的真实性。
四、“软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公共性,应当一概排除
“软肋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公共性。诚然,每个被告人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当我们在制度层面探讨这个群体时,他们就具有了公共性。当我们提及文化传统时,子女这个群体就具有了民族性;当我们提及新时代家庭观时,子女这个群体又具有了国家性。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永远相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下一代”手里。据此观之,整个“下一代”又何尝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软肋。因此,法律应当成为“软肋”们最坚强的后盾,而不是容忍其成为审讯策略的一部分。
综上,对于以被告人子女的合法权益相威胁而取得的供述,不必评估威胁的严重程度和被告人的痛苦程度,只要触及就应当一概排除。
作者:丁宇魁
时间:2023年06月18日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注:为了规避敏感词,故删除了部分语句。

